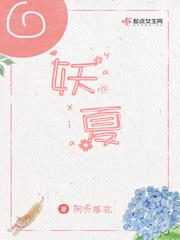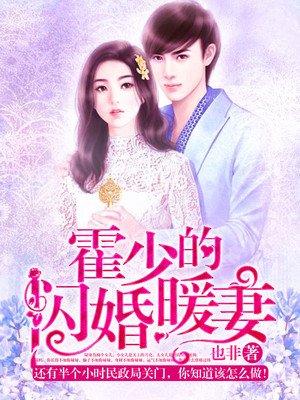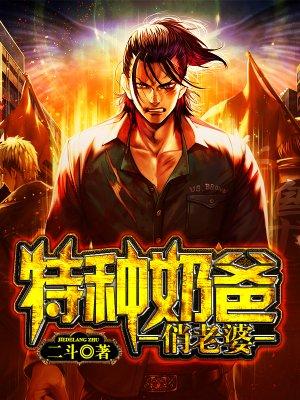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205章 雅乐之美 孔子听乐的心灵震撼(第1页)
子曰: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!”
子曰: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!”《论语?泰伯》中的这句赞叹,是孔子对西周雅乐极致魅力的生动描绘。师挚,作为鲁国乐官中的杰出代表,以精湛的技艺开启整场乐舞;《关雎》之乱,指《关雎》乐曲的终章,曲调恢弘悠扬,意境深远;“洋洋乎盈耳哉”则是孔子聆听后的直观感受——那美妙的乐声充盈耳畔,令人心潮澎湃,久久难忘。春秋时期,礼崩乐坏,雅乐逐渐衰落,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与雅乐,而这句赞叹,不仅是对一次具体听乐体验的记录,更是对雅乐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的高度认可。在当代社会,随着多元音乐文化的兴起,传统雅乐逐渐淡出大众视野,重新审视孔子这句箴言,探寻雅乐的魅力与价值,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丰富当代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。
一、溯源:春秋时期的雅乐文化与师挚其人
要理解孔子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!”的赞叹,首先需要回到春秋时期的雅乐文化背景,厘清雅乐的内涵、功能,以及乐官师挚的角色与地位——只有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语境,才能真正体会孔子听乐时的震撼与对雅乐的推崇。
(一)春秋时期的雅乐:礼仪与音乐的完美融合
雅乐,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宫廷正统音乐,与“礼”紧密结合,是礼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并非单纯的音乐形式,而是集诗歌、音乐、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,涵盖了祭祀、朝聘、宴饮、射礼等多种礼仪场景,承担着沟通人神、规范秩序、教化人心的重要功能。
西周时期,雅乐的创作与表演有着严格的规范。在内容上,雅乐多取材于《诗经》中的《雅》《颂》篇章,歌词蕴含着对先祖的赞颂、对时政的歌颂、对道德的倡导,如《周颂》中的《清庙》《维天之命》等,用于祭祀先祖,表达对祖先的崇敬;《大雅》中的《文王》《大明》等,歌颂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德,传递“仁政”“德治”的理念。在形式上,雅乐的乐器以编钟、编磬、琴、瑟、笙、箫等为主,曲调庄重典雅、节奏舒缓平稳,舞蹈动作整齐划一、雍容华贵,与礼仪的庄重氛围相契合。
雅乐的核心功能在于“教化”——通过音乐与礼仪的结合,潜移默化地向民众传递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。西周统治者认为,雅乐能够“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”(《礼记?乐记》),通过庄重典雅的乐声,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遵守等级秩序,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因此,雅乐被视为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。
到了春秋时期,随着周王室衰微,礼乐制度逐渐瓦解,雅乐也面临着衰落的危机。一些诸侯与卿大夫不再遵守雅乐的规范,转而追求通俗易懂、节奏明快的“郑卫之音”(民间音乐),雅乐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。孔子一生推崇周礼,对雅乐的衰落深感痛心,他曾感叹“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”(《论语?阳货》),认为“郑卫之音”放纵淫靡,会败坏社会风气,而雅乐的庄重典雅才是正道。因此,当孔子听到师挚演奏的雅乐时,才会发出“洋洋乎盈耳哉”的赞叹——这不仅是对乐声之美的欣赏,更是对雅乐正统地位的肯定与对礼乐文化的向往。
(二)师挚:春秋时期的雅乐传承者
师挚,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乐官,也是当时着名的音乐家,以精湛的雅乐演奏技艺闻名。在西周与春秋时期,乐官是雅乐的主要传承者与表演者,负责宫廷礼仪中的音乐演奏、乐舞编排以及音乐教育等工作。他们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演奏技艺,还需要熟悉礼仪规范,能够根据不同的礼仪场景选择合适的乐曲与舞蹈。
师挚作为鲁国乐官中的杰出代表,对雅乐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据《论语》记载,孔子曾多次与师挚交流音乐,对他的技艺与品德极为认可。“师挚之始”中的“始”,指的是乐舞的开篇部分,通常由乐官亲自演奏,奠定整场乐舞的基调。师挚以精湛的演奏技艺开启乐舞,其乐声庄重典雅、意境深远,瞬间将听众带入礼仪的庄重氛围中,为整场乐舞奠定了完美的开端。
除了演奏技艺高超,师挚还注重雅乐的教化功能。他在演奏雅乐时,不仅追求乐声的美感,更注重通过乐声传递道德理念与社会秩序。例如,在演奏《关雎》时,师挚通过悠扬舒缓的曲调,展现《关雎》中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(《论语?八佾》)的情感,引导听众树立健康的婚恋观与道德观。孔子对师挚的这种演奏理念极为认同,因此在听到师挚演奏的雅乐时,才会被深深打动,发出由衷的赞叹。
师挚的存在,代表了春秋时期雅乐传承者的坚守。在雅乐衰落的时代背景下,师挚依然坚持传承雅乐的正统技艺与教化理念,成为孔子推崇的对象。他的演奏,不仅让孔子感受到了雅乐的极致魅力,也让后人得以窥见春秋时期雅乐的风貌,为雅乐文化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印记。
二、解析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”:雅乐的结构与内涵
“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”,短短十个字,不仅记录了一次雅乐演奏的场景,更蕴含了雅乐的结构特点与文化内涵。“始”与“乱”是雅乐的重要结构组成部分,分别对应乐舞的开篇与终章;《关雎》作为雅乐的经典曲目,其内容与情感则体现了雅乐的教化理念。
(一)“始”与“乱”:雅乐的结构之美
在西周与春秋时期的雅乐中,“始”与“乱”是乐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,分别承担着“开篇定调”与“收束升华”的功能,二者相互呼应,构成了雅乐完整的结构体系。
1。“始”:开篇定调,营造氛围
“始”,即乐舞的开篇部分,通常由乐官亲自演奏,使用编钟、编磬等庄重的乐器,曲调平缓庄重,节奏稳定,其主要功能是奠定整场乐舞的基调,营造与礼仪场景相契合的氛围。
在祭祀礼仪中,“始”的乐声通常更为庄重肃穆,以编钟、编磬的厚重音色,表达对先祖的崇敬之情,引导参与者进入虔诚的状态;在朝聘礼仪中,“始”的乐声则更为典雅平和,体现诸侯之间的友好与尊重;在宴饮礼仪中,“始”的乐声则相对轻快,营造和谐愉悦的氛围。
“师挚之始”,即由师挚负责乐舞的开篇演奏。师挚作为鲁国最优秀的乐官,其“始”的演奏必然极为精湛——他能够根据礼仪场景的需求,精准把握乐声的基调与节奏,通过庄重典雅的乐声,瞬间将听众带入礼仪的氛围中,为整场乐舞奠定完美的基础。孔子对师挚的“始”极为赞赏,认为其乐声能够“洋洋乎盈耳”,可见师挚的开篇演奏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2。“乱”:收束升华,深化内涵
“乱”,即乐舞的终章部分,是雅乐结构的高潮与收束。与“始”的平缓庄重不同,“乱”的曲调更为恢弘悠扬,节奏更为丰富多变,通常会集合多种乐器共同演奏,舞蹈动作也更为舒展大气。其主要功能是对整场乐舞的主题进行升华,深化乐舞的文化内涵,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“《关雎》之乱”,即《关雎》乐曲的终章部分。《关雎》是《诗经?周南》的首篇,讲述了君子对淑女的爱慕之情,情感真挚纯洁,体现了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的中庸之道。《关雎》之乱通过恢弘悠扬的乐声,将这种纯洁的情感推向高潮,同时传递出“夫妇之道”是社会伦理基础的理念——只有夫妇关系和谐,才能实现家庭和睦、社会稳定。因此,《关雎》之乱不仅是乐声的高潮,更是文化内涵的升华。
孔子对《关雎》之乱的赞叹,正是因为它通过完美的乐声,将《关雎》的情感与理念传递得淋漓尽致,让听众在欣赏乐声之美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道德与伦理的力量。“洋洋乎盈耳哉”,不仅是对乐声充盈耳畔的直观描述,更是对《关雎》之乱文化内涵的高度认可。
(二)《关雎》:雅乐的情感与教化内涵
《关雎》作为雅乐的经典曲目,其情感与内涵是雅乐教化功能的集中体现。孔子曾评价《关雎》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认为其情感表达适度,既不过分放纵,也不过分悲伤,符合中庸之道,能够引导听众树立健康的情感观与道德观。
1。《关雎》的情感内涵:纯洁真挚的爱慕之情
《关雎》的歌词以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开篇,描绘了君子对淑女的爱慕之情。这种情感并非放纵淫靡的欲望,而是纯洁真挚的向往——君子通过“寤寐求之”“琴瑟友之”“钟鼓乐之”等方式,表达对淑女的爱慕,过程庄重典雅,符合礼仪规范。
在雅乐的演奏中,《关雎》的曲调与歌词的情感相契合,节奏舒缓平稳,音色柔和优美,既展现了君子爱慕之情的真挚,又不失庄重典雅。例如,在演奏“琴瑟友之”时,琴瑟的柔和音色能够细腻地展现君子对淑女的温柔情感;在演奏“钟鼓乐之”时,钟鼓的恢弘音色则能够展现君子对淑女的郑重追求,与礼仪的庄重氛围相契合。
妖夏
盛夏不老不死了上千年,看尽了想到想不到的各种热闹。没想到,她却也成了别人眼里的热闹,在一群不靠谱参谋的参谋下,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本闲初心不改,这本立志要写回言情了!...
闪婚厚爱:误嫁天价老公
简然以为自己嫁了一个普通男人,谁料这个男人摇身一变,成了她公司的总裁大人。不仅如此,他还是亚洲首富帝国集团最神秘的继承者。人前,他是杀伐果断冷血无情的商业帝国掌舵者。人后,他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,把她啃得连骨头也不剩。...
问道章
穿越加重生,妥妥主角命?篆刻师之道,纳天地于方寸,制道纹于掌间!且看少年段玉重活一世,将会过出怎样的精彩?...
霍少的闪婚暖妻
陆家有两个女儿,小女儿是天上的月亮,大女儿是阴沟里的死狗。陆妈你长得不如你妹妹,脑子不如你妹妹,身材不如你妹妹,运气不如你妹妹,你有什么资格过得好,有什么资格幸福?陆微言姐姐,你的钱是我的房子是我的,你男朋友也是我的。你就安心地当又穷又没人要的老处女吧。陆一语凭什么?我也肤白貌美大长腿好么?分分钟能找个男人...
神兵奶爸
啥,老子堂堂的漠北兵王,居然要当奶爸?好吧,看在孩子他妈貌若天仙的份儿上,老子勉强答应了...
万古天帝
人族少年叶寒,身怀神秘功法天帝诀,入大世界中,与群雄争霸,观万族并起!天地苍茫,今朝我主沉浮!小说关键词万古天帝无弹窗万古天帝txt全集下载万古天帝最新章节阅读...